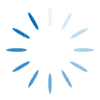三年前,盛夏。
温沐汐大四实习,隐瞒身份进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小设计公司。
公司里只有五个员工,她是其中之一。
沉星安是公司招来的兼职法务助理,一个沉默寡言的大二学生,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,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。
温沐汐注意到他,是因为他连续一周都在啃同一袋干硬的面包当午餐。
“呐,多买了一份三明治,吃不完了。”
某天中午,温沐汐把一份还温热的火腿三明治放在沉星安的办公桌上。
沉星安抬起头,那双过分好看的眼睛里全是警惕:“我不需要施舍。”
“不是施舍,是交易。”
温沐汐拉开他旁边的椅子坐下,“我听说你是A大法学院的?我毕业论文有个法律问题想请教,这算咨询费。”
她笑得坦荡,眼睛弯成月牙。
沉星安盯着她看了几秒,默默接过三明治。
那是他们第一次说话。
后来温沐汐发现,沉星安不仅是穷,他还在同时打三份工——白天在公司,晚上在便利店,周末去发传单。
他的手机永远调成静音,偶尔有电话进来,看到来电显示,他的脸色就会变得极其难看。
有一次加班到深夜,温沐汐去便利店买咖啡,正撞见沉星安被一个醉醺醺的中年男人揪着衣领辱骂。
“小杂种!让你还钱听不懂?你那个赌鬼老爸欠了老子三十万!父债子偿,天经地义!”
男人喷着酒气,扬手要打。
温沐汐想都没想就冲了上去。
“我已经报警了!”
她挡在沉星安面前,虽然声音发颤,但脊背挺得笔直,“这里有监控,你敢动手,我就让你进去蹲几天!”
男人被她的气势唬住,骂骂咧咧地走了。
温沐汐转过身,看到沉星安靠在货架上,脸色惨白如纸。
“你没事吧?”
她想碰碰他的手臂,他却像触电一样躲开。
“别管我。”
他的声音嘶哑,“我的事,你管不了。”
那天晚上,温沐汐固执地跟着沉星安,看着他走进城中村一栋摇摇欲坠的老楼。
楼道里堆满垃圾,墙上贴满了“欠债还钱”的红字报,其中一张上赫然写着沉星安父亲的名字。
“我爸是个赌鬼。”
沉星安忽然开口,声音在黑暗中飘忽不定,“我妈受不了,在我十岁那年跳楼了。他欠了一屁股债,每天都在躲债主。我考上大学那天,他偷走了我的录取通知书,想卖掉换钱。”
温沐汐的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。
“后来呢?”
“后来我报警了。”
沉星安笑了,那笑容比哭还难看,“警察找到他时,他正用我的身份证办高利贷。从那以后,我就搬出来了。但他欠的债,债主还是会找上我。”
他转过身,月光从破旧的窗户照进来,在他脸上投下破碎的光影。
“所以,离我远点,温沐汐。我是沼泽,靠近我的人,都会陷进来。”
温沐汐没有离开。
从那天起,她开始“不小心”多带一份午餐,“刚好”有电影票用不完,“碰巧”知道哪里有性价比高的出租屋。
她陪他去法律援助中心咨询,帮他整理债务材料,在他被债主堵门时,毫不犹豫地报警。
沉星安从一开始的抗拒,到后来的沉默接受,再到偶尔会露出极淡的笑容。
直到那个雨夜。
温沐汐加班到十点,走出公司时,看到沉星安蜷缩在街角的屋檐下,白衬衫上全是血。
“星安!”
她冲过去。
沉星安抬起头,额角的伤口还在渗血,但眼神却空洞得可怕。
“我爸死了。”
他轻声说,“债主找上门,他从六楼跳下去了。临死前,他给我发了条短信,说‘儿子,对不起’。”
温沐汐什么也没说,只是脱下外套裹住他颤抖的身体,拦了辆车带他去医院。
缝针的时候,沉星安一直很安静,只是死死攥着温沐汐的手。
从医院出来,已经是凌晨两点。
雨停了,街道空旷无人。
“我没有家人了。”
沉星安忽然说。
温沐汐停下脚步,转身看着他。
月光下,少年苍白的脸上还贴着纱布,那双总是戒备的眼睛里,第一次露出了脆弱。
“你还有我。”
温沐汐轻声说,“从今天起,我就是你姐姐。”
沉星安怔怔地看着她,许久,一滴泪从他眼角滑落,砸碎在水泥地上。
那是温沐汐第一次,也是唯一一次看到他哭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